重庆潼南古溪羊子养殖场
《世说新语》为什么没有收录陶渊明
谢邀!
《世说新语》是魏晋名士的“风流宝鉴”记载的是汉末至晋末约二百多年的士林风流。关于《 世说新语》 何以不收陶渊明的原因,各家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主要是陶氏家族在东晋没有取得世家大族的地位和声望所致。另一个是陶渊明那时的地位和影响远非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么重要。究其原因主要是陶渊明不是清谈之士,其次还有家世衰微破落、文风平淡等,在当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和足够的声誉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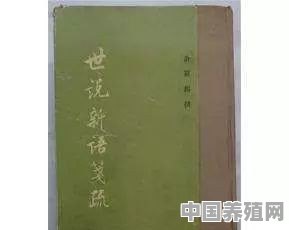
谢谢邀请!对于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为什么没有收录有关陶渊明的史迹的问题,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世说新语》中收集的大都是有官职有地位的人的史迹,大都在贵族阶层,下层百姓的东西根本没有。陶渊明年轻的时候在彭泽县做了几年小官,因看不惯官场,20多岁就归隐了,从此过的是躬耕自给的生活,是地地道道的贫苦农民,他的作品被收录的可能性太小,有可能没收录。二是今天看到的《世说新语》是残缺不全的,如果有人收录那必然在末卷,因为此书是按时间顺序编写,内容到东晋结束,陶渊明生在东晋末年,殁于南朝,从时间上看,属于编写末卷的范围。自然编辑了,今天看不到,那有可能遗失了。
你好,我是容千寻,文化领域爱好者,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为什么《世说新语》中没有关于陶渊明的记载?是陶渊明不配吗?陶渊明一生多次被征辟,只有他拒绝别人的份儿,这样的人怎么会不配出现在《世说新语》中吗?当然配。但是他却没出现,为什么呢?
是世家大族排斥陶渊明吗?我想应该也不是。魏晋是一个讲究风骨的年代。陶渊明越是归隐,名气就越大,所以很多人不停地请他出山。魏晋名士追求与崇尚的也正是陶渊明这样风度,那魏晋的名士出身于哪个家族?当然是世家大族。所以说世家大族排斥他似乎也说不通。
难道是刘义庆与陶渊明有什么私人恩怨?公元405年陶渊明就归隐了,立志不再做官,那时候刘义庆才2岁,肯定是谈不上利益纠缠了。你可能会问那日后呢?其实也不会。历史上对刘义庆的评价是“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一个是性情简素,没有很多功利俗欲,且爱好文义的人,另一个是淡泊名利,采菊东篱下的人,我觉得如果他们相识的话,他们只会是惺惺相惜。
说了诸多推测,都不对。那只有最后一个原因了,历史上记载《世说新语》原来共有8卷,但是有很多已经散佚了,现今之流传下3卷,所以我觉得最合理的推测就是: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陶渊明的趣事,但是非常不巧,有关陶渊明的记载遗失了。
以上都是个人浅见,欢迎批评指正。
我们知道《世说新语》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最重要的材料,但恰恰这部记录魏晋名士风流轶事的集子中并无陶渊明风流的只言片语。究竟什么原因呢,也是古今很多名家讨论的问题。
第一种说法:当他年轻时,由于籍隶南方寒族,官司阶又低,与贵人高门没有来往,不合本书选人的原则。
第二个原因:等他隐居柴桑,声名大噪时,时间又已经超出本书所包的时代之后了。”(文载《东方杂志》复刊十五卷第十二期1982年6月)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其家庭没有取得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不是名门望族。当时陶渊明家境贫穷日也有什么政治地位,虽然是当时为有名的隐士,可声名不显于上层贵族,自然上不为上层名士所,
所以,综合以上几点,针对《世说新语》缘何不录陶渊明,可以推论主要在于陶渊明本人,他不是清谈名士,文风平淡,脱离当时社会主流文坛,大众对他了解不多,又加之家世衰颓,作者刘义庆因个人原因对陶渊明的刻意回避。种种原因这才导致了《世说新语》不见陶渊明的遗憾。
魏晋世家大族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迅速膨胀,很快就转化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与日俱增,日益强化的门第观念。门第观念的核心是建立在经济条件极为富庶和政治势力极为强悍基础上的家族优越感;它以家族的自尊和排他为基本出发点,以不同流品之间的严格界限为基本表现特征,以婚姻、名讳和家教为主要表现形式,充溢于士族生活的各个角落。它是士族阶层经济和政治上获得空前膨胀的精神化、观念化的产物。这里着重谈《世说新语》一书所表现的士族门第流品意识。
初读《世说新语》时,有一疑惑久未得解:为何有晋一代诗坛祭酒陶渊明竟然不得入《世说新语》中?经深入把玩《世说》,方悟此乃《世说》编者及当时盛极一时的门第流品意识使然。陶氏一族晋代以陶侃最为知名[ii],但也常受人轻辱。《世说新语·容止》“石头事故”条载庾亮畏见陶侃,而温峤劝亮往之言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余嘉锡笺疏引述李慈铭言,认为“溪”当作“傒”,为“鸡”之误,乃前人对江西人之蔑语,犹呼北人为“伧父”。陈寅恪则以为“溪”为溪族,乃高辛氏女与畜狗所生后代。陶侃及陶渊明一族即出于溪族[iii]。周一良也支持陈说,并认为:“所谓溪人者,多以渔钓为业,如唐代蛮蜑渔蜑之比。”刘敬叔《异苑》(《津逮秘书》本):“钓禨山者,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一织梭,还挂壁上。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空而去。其山石山犹有侃迹存焉。”《世说新语·贤媛》亦载:“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鮓饷母。母封鮓付使,反书责侃。”所以周一良先生说:“盖陶公正是渔贱户之溪人,故贵显后犹不能逃太真之轻诋。”可见“溪狗”为人们对陶氏家族为狗裔的蔑称。正因为陶氏祖先有这样丑史,所以它一直受到人们(尤其是世家大族)的蔑视和嘲弄。 陶氏家族的地位变化始自陶侃。
其经过十分艰辛:陶公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髢,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刘注引《晋阳秋》:“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贫贱,纺绩以资给侃,使交结胜己。侃少为寻阳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宿。时大雪,侃家无草,湛彻所卧荐剉给,阴截发,卖以供调。逵闻之叹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岂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当相谈致。’过庐江,向太守张夔称之。召补吏,举孝廉,除郎中。时豫章顾荣或责羊晫曰:‘君奈何与小人同舆?’晫曰:‘此寒俊也。’”又引王隐《晋书》:“侃母既截发供客,闻者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进之于张夔,羊晫亦简之。后晫为十郡中正,举侃为鄱阳小中正,始得上品也。”)(《世说新语·贤媛》)
陶母截发留宾,传为千古美谈。但时过境迁,后人往往从道德和伦理角度,注意到陶母之贤德,却往往忽略了故事的原汁原味,是着意描绘和烘托出一个寒族家庭奔向贵族社会的坚定决心和艰难历程。陶母的丝丝乌发,未尝不是寒门对于士族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慢态度的强烈控诉。然而可悲的是,士族的强大势力使得寒族尽管心有不满,却又不得不惟命是从,亦步亦趋,按照士族的理念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人生道路。正因为陶氏家族的卑微出身,才使得尽管陶侃已经开始步入上流社会,但其他高门贵族仍然将其视为寒门。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陶氏家族的郡望至今仍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这本身就不是世家大族应有的缺憾。《晋书·陶侃传》记载:“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宋人汪藻《世说叙录·世说人名谱》中收录名门族谱凡二十六种,未见陶氏在内;另有二十六族无谱者,陶侃、陶范在列其中,未言郡望[vii]。直到唐代,陶家的郡望才在有关的姓望材料中被肯定为江州寻阳郡
